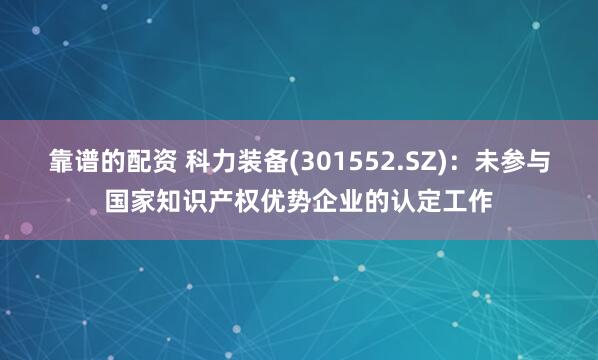煌煌中华,文脉如长江亘古流淌不绝。龟甲铜器之上镌刻最初天光;简牍帛书承载着文明最初的珍贵。更有蚕丝锦帛献上的柔软书卷,穿越光阴灼灼如故。孔圣人所谓“述而不作”,非真不作也杭州在线配资,乃是以敬畏之姿立言,承担那份如泰山压顶、又如磐石难移的文化托付!司马子长忍辱于《史记》,于幽暗之地点划春秋;孙膑残身而著兵书,在困境中开辟智谋的天地;屈原行吟泽畔,赤诚的《离骚》字字忠贞……。这一切都如丝不绝,在历史长河中凝为华夏文心那硬如骨骼的脊梁,不因烈火摧折而有丝毫弯曲。
韩退之秉“文以载道”之思于衰世,挽儒于将倾;张横渠立“为天地立心”宏大誓愿,成千古绝响,道破了士魂深处不熄的炬火。文人著书,皆“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王弼天才早慧流星般短暂的生命中注尽玄经,让《老子》《周易》在他的热血青春里发出振聋发聩的现代回响;玄奘自西天归来,于孤灯残照的寒夜孜孜译经;曹雪芹于茅屋“举家食粥”,呕心沥血著红楼,字如米珠薪桂更迭成绝唱。凡此种种,皆是华夏文魂不灭的见证,是心印千古未曾遗忘的文化胎记。
中华“心学”,实为一轴心性自觉见悟之磅礴长卷。自孟子“四端”如种子深植泥土般萌发开始,到陆象山“宇宙是吾心”的恢弘断言跨越时空,至阳明子“致良知”如太阳照亮九州三声呼唤响彻天地,旨在叩问那心中唯一而绝对的灵明光源。数千年来,先人们皓首穷经,以生命为柴薪,无非是为了将心灵深处那盏幽微而神圣的灯烛拨得更明亮一些。
展开剩余66%今有学人弓少星先生,沉潜史海哲思数载,其新著《心三识观》破云而出。通览全著,弓少星先生将儒释道贯通一道,将道和万维空间化演二数(时空数、因果数),将多维转化归于时时显隐之别,并言哲学只限“法”维二元次逻辑因果,神学将道虚拟形象化模糊,以及书中对万物“三性”论,属性、自性、天性之和合显化总因果等,均超越了命运之羁、阴阳之判、名相之显和学派之争,弓其此著,实乃在千载文枢沃土之中抽发出的一枝清雅而坚韧的新芽,更是对心学历程中重要追问展开深邃探索和突破创新的个体尝试。其以“三识”分灯为枢,“显识”于世俗尘埃中明晰事物真伪,犹如老子讲“解其纷、和气光、同其尘”;“蕴识”于历史层岩深处辨识民族文化的原始基因与古老回声,好似“知所从来,明其所往”;“化识”更指向文明与个体在时空洪流中融合后的终极超越,见证自性决定属性之显、源于天性之归。这些思悟不再是单一的内省烛照,而为心灵拓展出多重面向的广阔观照维度,将个体微弱精神置于如苍海奔腾的文明进化洪涛中重新审视自我与存在的时空意义。如此,弓少星先生乃于阳明心体之上开启新门,在新的轴心上延续王阳明的叩问,也是于古老灯座上点燃属于今人的心学新炬火。
薪火心传,亦非无艰。历史上,许多士人的著作得以传世并成名,往往非凭一己之力,而是依赖当世或后世权威的发现、推崇与传播。这种“现象”贯穿中国学术文化史,亦成为文化经典形成传世之立的重要动力。如董仲舒《天人三策》被汉武帝采纳,使儒家著作升格为治国经典。而《诗经》《尚书》等原为民间辑录,经朝廷整理、注释后成为“五经”。唐代孔颖达主持编修《五经正义》,将杜预注《春秋经传集解》定为科举标准,使个人学术成果通过官方面向全国士子推广。左思《三都赋》因张华、皇甫谧作序而洛阳纸贵,文人圈层的品评成为作品价值的“认证标签”。杜甫诗作在生前寂寥,经元稹撰《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推崇其“尽得古今之体势”,中唐后始被尊为“诗圣”。朱熹注释《四书》整合程颢、程颐之说,构建理学体系,门徒广传其书,终使程朱之学成为元明清科举核心。再有顾炎武《日知录》在清初仅为手稿,经潘耒刊刻并作序阐发其经世思想,方成启蒙思潮基石。《聊斋志异》初被视为志怪小说,经王士禛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引发文人关注,晚清后因其社会批判性被奉为经典。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在乾嘉时被斥为异端,清末梁启超、胡适重评其反理学价值,确立其哲学史地位。这些著作皆是从“当代冷遇”到“永恒经典”的蜕变。历史真实回响,个体创作因推荐而超越时空,融入历史文化精神血脉;而推荐者的眼光,亦成为历史对其自身智慧的考验,发见学术盛微道术之鉴。
《心三识观》初成之际,宛如薪火初燃于心学宇宙之中。愿书页如无数个微弱灯盏相连为星河,照亮后来人探索心性迷宫的曲径幽途。此焰如星,却是多维文明深埋于人心岩层之下的火种再度复燃,突破心膜维界众化得明;其光初煜,却已蕴含穿透未来的心灯永薪,携手哲学、科学、神学共赴道途。
黄勇
乙巳年荷月于燕园未名湖畔杭州在线配资
发布于:山东省富华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